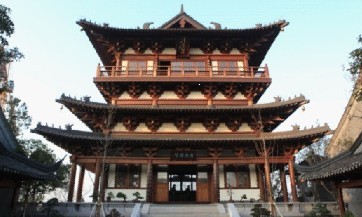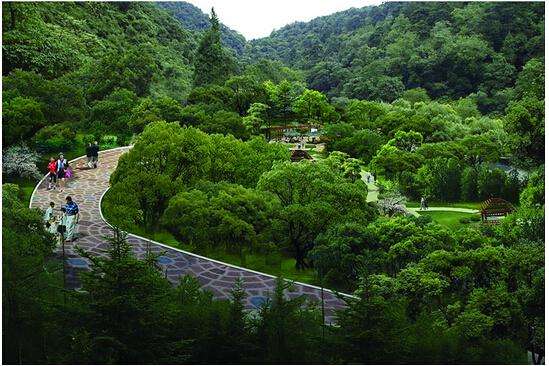走进研究会
图文推荐
论镇江保卫战中的社会治安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18-05-25 阅读数:
论镇江保卫战中的社会治安
孙洪军
【提 要】 1842年7月镇江保卫战前后,由于文武官员的渎职行为,造成镇江府城陷落,许多百姓封闭城中,遭受战乱摧残;在肃奸固城过程中,犯了扩大化错误,无辜百姓惨遭屠杀;城乡失序,抢掠横行,百姓生命财产遭受不法侵害,造成严重的战时社会治安灾难。
【关键词】 镇江保卫战;社会治安;政治腐败
在清代,镇江城是常镇道治、镇江府治、丹徒县治所在地,也是驻防旗兵镇江副都统衙门所在地。道员、知府、知县是守土官,副都统是专城防守官,他们对保卫镇江城市、维护镇江的社会治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地方职官的治安职掌
1. 镇江文武官员的治安职责
在清代,各省布政、按察两司之下各设分守、分巡道,分守、分巡道职掌“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励风俗,简军实,固封疆,以帅所属而廉察其政治。”[1]3355镇江城属于常镇通海道管辖,常镇通海道简称常镇道,驻镇江丹徒县。常镇道兼兵备衔,清代规定:“凡守、巡道加兵备衔者,即可节制所辖境内之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成为‘简军实、固封守’的文武地方长官。”[2]198常镇道上马能管军,下马可管民,职掌广泛,其主要职责是对社会治安有重要影响的刑名司法,如考核官吏政绩、督捕命盗逃犯、维护社会秩序等。
清代在镇江城设镇江府,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知府的佐贰官同知、通判,“分掌管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夷诸要职。”[1]3356作为一府之长的知府负有重要的治安职责。府一级政府治安方面,主要起督促作用,将中央各部、省督抚衙门、司道衙门的咨文、札饬转发州县,督促所属州县“朔望宣讲圣谕、联保甲、勤理词讼等。”[2]164这种督促作用主要表现为承上启下,即部、督抚、司道层层咨、札至府,再由府札催各州县组织实施。地方发生的治安案件,知府每年都要申报两司。府的佐貮官通判,称“捕厅”,负有缉捕、协缉所属州县要犯、逃犯之责,并且还负责府属地方社会治安的日常事务。
治所在镇江城的丹徒县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1]3357维护社会治安是州县等基层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对州县官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清代州县官的治安职责,一是组织建设,力行保甲之法;二是率领佐貮杂职、书吏、差役,督催各乡保完成禁盗贼、禁邪教、禁赌博、禁娼妓、禁打架、禁讼师、禁私宰、禁私铸、缉捕等经常性的治安任务。”[2]108州县政府维护治安坚持“严其缉捕,力行保甲”的方针。所谓严其缉捕,就是一旦发生命盗重案,州县官要不辞辛劳、不避风雨,立即率领所属捕役、仵作、刑名书办,会同驻军营汛官兵,飞速赶赴出事地点,进行勘察检验,当场询取确实供词,委派捕役,给足经费,促其全力缉捕真凶,并监禁捕役的家属,作为人质,使其不能在外逍遥,贻误公干。所谓力行保甲,就是坚持预防为主,推行保甲制度,防范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知县之下有佐貮官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1]3356
为了加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汉民的控制,清政府实行八旗驻防制度,顺治十六年(1659年)在镇江置京口副都统。京口副都统是专城副都统,清制:“专城副都统,正二品,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1]3383京口副都统对保卫镇江城,调和军政与军民关系,维护镇江的社会治安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严重的渎职失职行为
在封建时代,百姓是朝廷的赤子,职官是百姓之父母,无论平时还是战时,维护社会安定,爱护百姓,切实保护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是朝廷命官的基本职责。但是,在镇江保卫战前后,对镇江守土有责的各级官吏却不能尽职尽责,维护一方安全,存在着或轻或重的渎职失职行为。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1842年7月),两江总督牛鉴从苏州经镇江回江宁,他命令镇江富户凑集十二万两银子作为镇江的赎城费,以“犒夷师,俾不登岸”,借以保护镇江城不受英军蹂躏。集资赎城、花钱消灾的合理合法性暂且不论,但是,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提前布置是这一指令得以实施的关键。镇江富户已经十室九迁,不能凑够预定十二万两的数目,牛鉴仓皇逃回江宁,置镇江于不顾。本来,镇江作为江河交会处之著名商埠,富庶之名天下皆知。凑集十二万两,“亦甚易易,使兵不战,令可猝下,使民输金,命必先申,制府于此少经营耳。”[3]41-42对镇守镇江负有直接责任的常镇道对守土备战持消极态度:“署常镇道张琴,久住扬州,收纳课税,于地方一切事宜并未筹画”[4]98不仅如此,道员对所属府州县的社会治安、缉捕逃犯等司法行政管理负有监督检查之责任。清律规定:“如果所属府州县出现重大治安、司法行政管理的问题,该管道也将受到失察处分,甚至受到刑事惩办。”[2]200在此,常镇道的渎职行为是十分明显的。
是年六月十二日,镇江府城城门关闭,缺少物资,市场亦随之关闭。百姓无粮可买,无米下锅,因而合城炊烟寥寥,面临断炊挨饿的危险。监生吴学增家有米四百余担,储藏在西城外,吴学增“呈请郡守祥麟,运入城安民,郡守转请副都统,仍不开城,谓开城吾辈命即休,不能顾百姓,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海龄不顾百姓死活,激化满汉矛盾,显然有违其职守。其实,海龄在关闭城门禁止民人出入期间,每日仍开西小门进兵,如果顺便将吴学增家数百担米带入城中,给食百姓,本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副都统居心叵测,导致百姓人人疑惧。“日晡,在城孝廉诸生十多人,复至府署为饥民请命,署中空无人,惟教官四,分日到府伴太守,太守不肯复与都统言,众乃太息而归。”[3]42-43在百姓最需要知府履行职责保护百姓的时候,知府却知难而退,放弃职守,其失职行为实堪痛恨。
该年六月,英舰尚在上海,镇江副都统海龄惊慌失措,将北门外防守江边的青州兵全部撤入城内,城门辰启申闭,百姓惊恐慌乱,纷纷迁避。两江总督牛鉴讥讽他张皇恐众,海龄出示安民公告,历数长江下游重重天险,判断夷船断不能驶入,即使英舰驶入,则“本副都统立即提兵出击,已有制胜奇策,尔民无得摇惑迁徙”,[3]75海龄虚张声势,调动防兵,仅在城市四门添设部分枪炮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镇江的防卫能力,是对镇江人民的欺骗,客观上麻痹了百姓,延缓了百姓的迁徙进程,造成重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是失职误事之举。难怪梁廷枬批评海龄“又不知预备守具,与团练民间丁壮协守”,导致镇江城破,在镇江“夷人焚掠惨逾他县”[5]117,镇江人民遭受巨大创伤。对于失陷城池,《大清律例•兵律•军政•主将不固守》条例规定:凡沿边、沿海及腹里府、州、县与武职官同住一城者,被贼攻陷城池,劫杀焚烧者,武职拟斩监候,“其府、州、县掌印并捕盗官,俱比照守边将帅被贼侵入境内掳掠人民律,发边远充军。其守、巡道官,交部分别议处提问。”[6]314镇江守土有责的文武众官战后受到严肃处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失职误事,却给镇江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城陷前后的治安灾难
英军攻城之前,海龄在劝民出城与阻民出城之间摇摆不定,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阻止百姓逃离镇城的,这就加重了镇城陷落后百姓生命财产受损的程度。
1. 阻民出逃,百姓惨遭杀戮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英舰进入长江口。镇江城内流言四起,内外居民无不警扰,百姓纷纷迁徙。海龄散布旗兵、捉拿汉奸,旗兵乘机劫掠:“每有妇人孺子见旗兵警走,即追而杀之,向都统报功获赏矣。”[3]75初八日,英舰逼近镇江,居民络绎不绝仓皇外逃;但是,守城旗兵仅开启一扇城门让百姓通行,城门开启时间仅有一个小时,其间“驻防旗兵,交刃对立,使行者匍匐从刀下过,稍举首即触刀流血被面,除随身衣服外,一物不许携带,带者立行夺下。人方络绎行,突然闭门,有子弟出而父兄闭入城内者,有妻女出而丈夫闭入城内者,城内外呼号之声,惨不忍睹。”[3]42 十四日, 英军攻入北城,“知府祥麟随至,请开门放难民,副都统畏人指摘,意欲独窜,仍不允,反以鸟枪击众,众警散。” [3]43难怪时人杨棨控诉海龄:“两手牢握四门锁钥,西门破则率兵开东门走,北门破则率兵开南门走,而城中百姓,禁闭不许出城,破城刃死,不破城饿死,殆欲尽死百姓专生官与兵也。误国殃民,莫此为甚。”[3]46镇江陷落后,海龄自杀身亡,“夷鬼沓来,不移时,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未死者多被拥抱而去,生死离散,目不忍睹。”[3]43镇江百姓遭受空前的战争灾难。
2. 查拿汉奸,海龄滥杀无辜
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是影响反侵略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学界已多有论述。镇江军政当局也高度重视防范汉奸的破坏行为。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天,“数月镇江城门辰巳时启,或未暮即闭,严诘奸寇。”[7]39事实上,在镇江保卫战中,确实有少数民族败类通敌叛国,甘当汉奸,如1842年“7月15日之战中英军一队就是汉奸‘导引’下乘小艇企图在焦山南岸登陆;21日攻城时英军一部又在‘北固寺僧’密指下从十三门乘虚登城,这从反面证明海龄的禁严措施实属必要。”[4]98-99在英军攻城的关键时刻,有“登城而呼寇者”[8]680则完全站在侵略者的一边助纣为虐,成为可耻的民族败类。在百姓看来对汉奸进行严惩,“杀呼寇之民,以肃军律,要亦非残民以逞也。”[8]680其实,对通敌叛国的汉奸进行严惩,在当时是有法律依据的,《大清律例•兵律•关津盘诘奸细》规定:“境内奸细,走透消息于外人……盘获到官,须要鞠问接引入内、起谋出外之人,得实,不论首从,皆斩。”[6]331但是,海龄在搜捕汉奸的过程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英军攻城前“虚传说城中藏有奸细,沿户搜索,稍可疑者即受诛戮,城内人人惕息。”[5]117“闭城之先,副都统即疑满城皆是汉奸,日抓数人送邑令提讯,邑令钱燕桂讯明释放,即指钱令为汉奸,乘其出城,闭门不纳。”海龄指民为奸的鲁莽之行恶化了满汉关系,激化了民军矛盾,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海龄多持批判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闭城以后,“凡他邑人城中习懋迁者,充工役者,作僧道者,为仆及行乞者,以非土音,均被缚去,略一诘问,即杀十三人于小教场,其众人具保状证为良民者,不得以竿掷城外,免于斧钺,复死于倾跌。而里巷中晓行者,暮行者,与夫行城下者,不问何人,胥用鸟枪击毙草莽无算。”[3]42由于军政当局疏散城中百姓的措施不利,镇江城内一部分士绅、百姓未能及时外逃,遭受兵燹之灾,兼之旗兵在搜捕汉奸过程中错误地伤害了一些无辜平民,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海龄的指责胜过赞扬,“但战争是残酷的,从战争的要求看这些措施实无可厚非。”[4]98-99
3. 抢掠横行,土匪肆无忌惮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英舰抵达圌山,镇江府城四门关闭,市民惊惧,纷纷罢市。“奸民以城闭,法令不行,遂聚众抢掠,各店铺米谷,所至一空。城内外一日数十起。”初九日,提督刘永孝在西门外驻地对抢掠者以军法从事,公开处决抢劫暴徒一人,一人被割去耳朵,而镇江城内“民愈乱,抢掠公行。”初十日,“南门外犹抢掠不已,兵备道与县令驻都天庙,奉提督令斩一人,鞭朴数人,奸民乃少戢。”[3]77 十四日,镇江城破,城中文武官员或死或逃,镇江陷入权力真空之中,社会失序,奸民与英夷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居民导夷鬼劫掠,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夷鬼止取金银,衣服等物件,悉归导者。导者多其家之邻友亲族与夫豢养仆人。十七日,伪提督出示禁劫掠,而劫掠如故。四乡男妇闻风亦至,土匪十倍于夷 。夷鬼止烧官房,而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重垣峻宇,尽成瓦砾场,皆土匪所为。初放火时,夷目曾缚十五人于观音庵大树上,鞭背流血,而纵火如故,夷亦无法可施。惟言经过数省,人心之坏,未有如此郡者。”[3]44-45更为可恶的是,乡下奸民闻知镇江城内抢掠成风,也趁火打劫,结伙入城参与抢劫:“廿四日,越河大港乡民二千蜂拥入城,持械抢掠,势不可挡。”[3]45英军的炮火轰击,兼之英军与土匪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使古城镇江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被占各城中损失最大、百姓处境最惨的中国城市。
三、酿成镇城治安灾难的根源
1. 政治腐败,官不履职
清朝统治阶级目光短浅,孤陋寡闻,对近代战争一无所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英军攻占宁波,两江总督裕谦投水殉节,江南震动。在扬州,士绅集资募勇,积极防御。路过扬州的新任福建汀漳龙道张集馨不以为意:“余思英夷在浙,距扬尚远,乡人胆薄,先自张皇。须知英舟笨重,内河断不能至。且英人所恃者惟舟,舍舟便无伎俩,何必纷纭杂沓,议守议迁?”[9]58当英舰抵达上海,马上溯江而上时,镇江副都统海龄更是虚张声势狂妄自大:认为夷船断不能驶入,即使英舰驶入,则“本副都统立即提兵出击,已有制胜奇策,尔民无得摇惑迁徙”。[3]75千百年来沉浸在天朝上国虚荣幻想中的封建官僚们闭目塞听,夜郎自大,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因而备战不足,最终导致丧师失地,城破民伤的严重战争灾难。
战前,文武官员议战议守,动摇不定,准备不充分,在英舰抵达镇江下游圌山时,“连日都统连府县各令宅眷出城逃去。”[3]76当英军围城,饥民无处买米,面临困境,部分知识分子勇敢担当责任,监生吴学增申请将城西门外他家400担米运进城中救济饥民时,郡守祥麟转请副都统,仍不开城,海龄以“开城吾辈命即休,不能顾百姓,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相回应,可见海龄把守住镇江城市、保证旗兵旗人生命作为第一要务,而把广大市民的生死置之度外,民之不存,要城何用?
战后,对于叛国投敌的汉奸,《江宁条约》明文规定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10]32以此之故两江总督张贴公文“榜谕汉奸,大意谓既往不咎,有控告者反坐。”[3]51百姓对此疑惑不解尚且有情可原,对于镇江陷落前后公开抢劫的违法犯罪分子,清律明文规定给予严惩:“凡强盗已行……但得事主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强盗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并积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随即奏请审决枭示。”[6]377-378法律虽有明文规定,政府居然敷衍了事,并不实力追究:“居民回城,知家中为某某所掠,不胜其愤,或鸣官指控,大宪亦多委干员办理,干员率多措置任意,听差役上下,于是差役至被告家夺其赃物,又至原告家讹诈,残灰遗瀋,扫地无余,于是民复有怨恨致死者,而差之富横如旧焉。”[3]73官员渎职、胥吏枉法导致政治腐败,可谓积重难返。
2. 民族矛盾尖锐,相互仇视
满官与汉官之间矛盾重重。虽然清政府一再表示满汉一家,不分畛域,但是,终清一代,满汉民族矛盾始终是十分尖锐的,这也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排满”口号作号召的重要原因。在镇江保卫战中,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更是显而易见:“闭城之先,副都统即疑满城皆是汉奸,日抓数人送邑令提讯,邑令钱燕桂讯明释放,即指钱令为汉奸,乘其出城,闭门不纳。城中守土官惟知府一人,与副都统为姻娅,听其所为,无能阻止。”[3]42当城中百姓缺少米粮,在城孝廉诸生十多人至知府衙门为饥民请命,请知府向副都统海龄商议,“太守不肯复与都统言,众乃太息而归。”[3]43汉民对满民也充满敌视。海龄的错误加速了镇江城市陷落的进程,百姓处境悲惨:“夷鬼沓来,不移时,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未死者多被拥抱而去,生死离散,目不忍睹。”部分汉民将对旗兵的愤怒转嫁到在城旗民的身上:“旗营中亦有未及出城者,叩户乞留,家家譟逐,无已跳入空宅中,坠厕箐,触树石者甚多,匿久则多饿死承尘土檐溜间。其妇女不能逾垣,又难匿迹,每伏池内,大半溺死,或出水潜逃,浮萍占满面上,望之如蓝面鬼然。”[3]43
汉民痛恨回民抢劫。时人认为不论城民乡民,肆意抢劫“固属同恶,而首恶犹在回民。白布裹头,持刀入人家,千百成群,所得金帛充栋,并衢巷亦为之满塞,前后巷口,不许民人出入,意犹未足。”[3]47回民甚至追踪逃难富户,假托为其看护家园,肆意勒索巨款,富户不从,则立毁坏其宅第,目无法纪,莫此为甚。汉满回民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动乱,危害社会的安定与民族的团结。
3. 道德沦丧,自相残害
镇江是座大爱之城,镇江百姓具有怜贫惜孤的优良传统:“镇江之民,一逢旱涝之灾,虽家近中人之产,无不捐赈,动以一二十万金为常,而平时有育婴、恤嫠、留养、救生、施药、施棺,以及给寒衣,散年钱储善举,无微不至,富家出资,寒士亦多出力,桑梓之情已至厚”,但镇江陷落前后,城乡奸民乘机抢劫,“力不能移之物,亦不肯留,必断碎烧毁而后去,若宿愿甚深者,人无心肝,至此已极。”[3]47 《江宁条约》签订后,居民返回城中家园,满目苍凉,遍地瓦砾,恰似人间地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夷抢掠之后,百里之内土匪结伙成百上千,执掌武器,入城搜刮,钱财衣物扫地净尽,妄顾礼仪,灭绝人伦:“其叔占侄资,甥掘舅藏,比比皆是。属离道绝,人貌兽心,吾郡祸其犹未艾乎?”[3]72读书之人参与抢劫者所在多有,士之劣者,本无为恶之才,也“穿壁逾墙,无所不至。昨丹阳令始捕一冯姓老诸生,赃至数千,法当斩,恨漏网者尚多耳。”[3]47镇江东码头一张姓生员,“至夷船报机密事,言议和是诱计,大兵已将至矣。夷首赏番银四百”,该生还与另外两名生员到丹阳,假托英夷索要军需物品,勒索丹阳县令准备大批物资解送镇江,后因其阴谋暴露而潜逃,对此,时人慨叹:“士习之坏,为古所未有。此三者实镇城之豺虎蛇蝎。”[3]47更为令人气愤的是,有些读书知礼的文化人也叛国投敌甘做汉奸:“有一诸生赴府署上书,为夷所摈。又有诸生二十多人,具牒乞充里长,伪提督坐鼓楼下亲给执照,分持而去。”[3]45
在镇江保卫战中,清军武官不能统筹全局、坚守城池,文官不能维护治安、疏散民众,城乡奸民乘机肆意烧杀抢掠,士人不能表率乡里却投敌叛国,乘机抢掠,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镇城失陷,理所当然,故时人愤怒慨叹:“镇城经此番蹂躏,破碎不堪,非夷人破碎之,镇人自破碎之也。”[3]46
战争时期的城市社会治安迥异于和平时期的社会治安,是非常态下的社会治安。军政当局在不能将百姓纳入战时体制、实现全民皆兵共赴国难的情况下,应该未雨绸缪,及时疏散百姓出城,尽量减少百姓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各级官吏亦需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切实维护战时社会稳定,最大限度确保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这就是镇江保卫战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3)[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4]严其林.镇江之战中的海龄[J].军事历史研究,2003(1):98-99.
[5]梁廷枬.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田涛,郑秦.大清律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7]许进,徐苏.陈庆年文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 :39.
[8]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四)[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9]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58.
[1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M].北京:三联书店,1957:32.
(作者为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副教授)
孙洪军
【提 要】 1842年7月镇江保卫战前后,由于文武官员的渎职行为,造成镇江府城陷落,许多百姓封闭城中,遭受战乱摧残;在肃奸固城过程中,犯了扩大化错误,无辜百姓惨遭屠杀;城乡失序,抢掠横行,百姓生命财产遭受不法侵害,造成严重的战时社会治安灾难。
【关键词】 镇江保卫战;社会治安;政治腐败
在清代,镇江城是常镇道治、镇江府治、丹徒县治所在地,也是驻防旗兵镇江副都统衙门所在地。道员、知府、知县是守土官,副都统是专城防守官,他们对保卫镇江城市、维护镇江的社会治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地方职官的治安职掌
1. 镇江文武官员的治安职责
在清代,各省布政、按察两司之下各设分守、分巡道,分守、分巡道职掌“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励风俗,简军实,固封疆,以帅所属而廉察其政治。”[1]3355镇江城属于常镇通海道管辖,常镇通海道简称常镇道,驻镇江丹徒县。常镇道兼兵备衔,清代规定:“凡守、巡道加兵备衔者,即可节制所辖境内之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成为‘简军实、固封守’的文武地方长官。”[2]198常镇道上马能管军,下马可管民,职掌广泛,其主要职责是对社会治安有重要影响的刑名司法,如考核官吏政绩、督捕命盗逃犯、维护社会秩序等。
清代在镇江城设镇江府,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知府的佐贰官同知、通判,“分掌管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夷诸要职。”[1]3356作为一府之长的知府负有重要的治安职责。府一级政府治安方面,主要起督促作用,将中央各部、省督抚衙门、司道衙门的咨文、札饬转发州县,督促所属州县“朔望宣讲圣谕、联保甲、勤理词讼等。”[2]164这种督促作用主要表现为承上启下,即部、督抚、司道层层咨、札至府,再由府札催各州县组织实施。地方发生的治安案件,知府每年都要申报两司。府的佐貮官通判,称“捕厅”,负有缉捕、协缉所属州县要犯、逃犯之责,并且还负责府属地方社会治安的日常事务。
治所在镇江城的丹徒县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1]3357维护社会治安是州县等基层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对州县官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清代州县官的治安职责,一是组织建设,力行保甲之法;二是率领佐貮杂职、书吏、差役,督催各乡保完成禁盗贼、禁邪教、禁赌博、禁娼妓、禁打架、禁讼师、禁私宰、禁私铸、缉捕等经常性的治安任务。”[2]108州县政府维护治安坚持“严其缉捕,力行保甲”的方针。所谓严其缉捕,就是一旦发生命盗重案,州县官要不辞辛劳、不避风雨,立即率领所属捕役、仵作、刑名书办,会同驻军营汛官兵,飞速赶赴出事地点,进行勘察检验,当场询取确实供词,委派捕役,给足经费,促其全力缉捕真凶,并监禁捕役的家属,作为人质,使其不能在外逍遥,贻误公干。所谓力行保甲,就是坚持预防为主,推行保甲制度,防范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知县之下有佐貮官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1]3356
为了加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汉民的控制,清政府实行八旗驻防制度,顺治十六年(1659年)在镇江置京口副都统。京口副都统是专城副都统,清制:“专城副都统,正二品,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1]3383京口副都统对保卫镇江城,调和军政与军民关系,维护镇江的社会治安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严重的渎职失职行为
在封建时代,百姓是朝廷的赤子,职官是百姓之父母,无论平时还是战时,维护社会安定,爱护百姓,切实保护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是朝廷命官的基本职责。但是,在镇江保卫战前后,对镇江守土有责的各级官吏却不能尽职尽责,维护一方安全,存在着或轻或重的渎职失职行为。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1842年7月),两江总督牛鉴从苏州经镇江回江宁,他命令镇江富户凑集十二万两银子作为镇江的赎城费,以“犒夷师,俾不登岸”,借以保护镇江城不受英军蹂躏。集资赎城、花钱消灾的合理合法性暂且不论,但是,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提前布置是这一指令得以实施的关键。镇江富户已经十室九迁,不能凑够预定十二万两的数目,牛鉴仓皇逃回江宁,置镇江于不顾。本来,镇江作为江河交会处之著名商埠,富庶之名天下皆知。凑集十二万两,“亦甚易易,使兵不战,令可猝下,使民输金,命必先申,制府于此少经营耳。”[3]41-42对镇守镇江负有直接责任的常镇道对守土备战持消极态度:“署常镇道张琴,久住扬州,收纳课税,于地方一切事宜并未筹画”[4]98不仅如此,道员对所属府州县的社会治安、缉捕逃犯等司法行政管理负有监督检查之责任。清律规定:“如果所属府州县出现重大治安、司法行政管理的问题,该管道也将受到失察处分,甚至受到刑事惩办。”[2]200在此,常镇道的渎职行为是十分明显的。
是年六月十二日,镇江府城城门关闭,缺少物资,市场亦随之关闭。百姓无粮可买,无米下锅,因而合城炊烟寥寥,面临断炊挨饿的危险。监生吴学增家有米四百余担,储藏在西城外,吴学增“呈请郡守祥麟,运入城安民,郡守转请副都统,仍不开城,谓开城吾辈命即休,不能顾百姓,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海龄不顾百姓死活,激化满汉矛盾,显然有违其职守。其实,海龄在关闭城门禁止民人出入期间,每日仍开西小门进兵,如果顺便将吴学增家数百担米带入城中,给食百姓,本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副都统居心叵测,导致百姓人人疑惧。“日晡,在城孝廉诸生十多人,复至府署为饥民请命,署中空无人,惟教官四,分日到府伴太守,太守不肯复与都统言,众乃太息而归。”[3]42-43在百姓最需要知府履行职责保护百姓的时候,知府却知难而退,放弃职守,其失职行为实堪痛恨。
该年六月,英舰尚在上海,镇江副都统海龄惊慌失措,将北门外防守江边的青州兵全部撤入城内,城门辰启申闭,百姓惊恐慌乱,纷纷迁避。两江总督牛鉴讥讽他张皇恐众,海龄出示安民公告,历数长江下游重重天险,判断夷船断不能驶入,即使英舰驶入,则“本副都统立即提兵出击,已有制胜奇策,尔民无得摇惑迁徙”,[3]75海龄虚张声势,调动防兵,仅在城市四门添设部分枪炮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镇江的防卫能力,是对镇江人民的欺骗,客观上麻痹了百姓,延缓了百姓的迁徙进程,造成重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是失职误事之举。难怪梁廷枬批评海龄“又不知预备守具,与团练民间丁壮协守”,导致镇江城破,在镇江“夷人焚掠惨逾他县”[5]117,镇江人民遭受巨大创伤。对于失陷城池,《大清律例•兵律•军政•主将不固守》条例规定:凡沿边、沿海及腹里府、州、县与武职官同住一城者,被贼攻陷城池,劫杀焚烧者,武职拟斩监候,“其府、州、县掌印并捕盗官,俱比照守边将帅被贼侵入境内掳掠人民律,发边远充军。其守、巡道官,交部分别议处提问。”[6]314镇江守土有责的文武众官战后受到严肃处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失职误事,却给镇江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城陷前后的治安灾难
英军攻城之前,海龄在劝民出城与阻民出城之间摇摆不定,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阻止百姓逃离镇城的,这就加重了镇城陷落后百姓生命财产受损的程度。
1. 阻民出逃,百姓惨遭杀戮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英舰进入长江口。镇江城内流言四起,内外居民无不警扰,百姓纷纷迁徙。海龄散布旗兵、捉拿汉奸,旗兵乘机劫掠:“每有妇人孺子见旗兵警走,即追而杀之,向都统报功获赏矣。”[3]75初八日,英舰逼近镇江,居民络绎不绝仓皇外逃;但是,守城旗兵仅开启一扇城门让百姓通行,城门开启时间仅有一个小时,其间“驻防旗兵,交刃对立,使行者匍匐从刀下过,稍举首即触刀流血被面,除随身衣服外,一物不许携带,带者立行夺下。人方络绎行,突然闭门,有子弟出而父兄闭入城内者,有妻女出而丈夫闭入城内者,城内外呼号之声,惨不忍睹。”[3]42 十四日, 英军攻入北城,“知府祥麟随至,请开门放难民,副都统畏人指摘,意欲独窜,仍不允,反以鸟枪击众,众警散。” [3]43难怪时人杨棨控诉海龄:“两手牢握四门锁钥,西门破则率兵开东门走,北门破则率兵开南门走,而城中百姓,禁闭不许出城,破城刃死,不破城饿死,殆欲尽死百姓专生官与兵也。误国殃民,莫此为甚。”[3]46镇江陷落后,海龄自杀身亡,“夷鬼沓来,不移时,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未死者多被拥抱而去,生死离散,目不忍睹。”[3]43镇江百姓遭受空前的战争灾难。
2. 查拿汉奸,海龄滥杀无辜
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是影响反侵略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学界已多有论述。镇江军政当局也高度重视防范汉奸的破坏行为。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天,“数月镇江城门辰巳时启,或未暮即闭,严诘奸寇。”[7]39事实上,在镇江保卫战中,确实有少数民族败类通敌叛国,甘当汉奸,如1842年“7月15日之战中英军一队就是汉奸‘导引’下乘小艇企图在焦山南岸登陆;21日攻城时英军一部又在‘北固寺僧’密指下从十三门乘虚登城,这从反面证明海龄的禁严措施实属必要。”[4]98-99在英军攻城的关键时刻,有“登城而呼寇者”[8]680则完全站在侵略者的一边助纣为虐,成为可耻的民族败类。在百姓看来对汉奸进行严惩,“杀呼寇之民,以肃军律,要亦非残民以逞也。”[8]680其实,对通敌叛国的汉奸进行严惩,在当时是有法律依据的,《大清律例•兵律•关津盘诘奸细》规定:“境内奸细,走透消息于外人……盘获到官,须要鞠问接引入内、起谋出外之人,得实,不论首从,皆斩。”[6]331但是,海龄在搜捕汉奸的过程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英军攻城前“虚传说城中藏有奸细,沿户搜索,稍可疑者即受诛戮,城内人人惕息。”[5]117“闭城之先,副都统即疑满城皆是汉奸,日抓数人送邑令提讯,邑令钱燕桂讯明释放,即指钱令为汉奸,乘其出城,闭门不纳。”海龄指民为奸的鲁莽之行恶化了满汉关系,激化了民军矛盾,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海龄多持批判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闭城以后,“凡他邑人城中习懋迁者,充工役者,作僧道者,为仆及行乞者,以非土音,均被缚去,略一诘问,即杀十三人于小教场,其众人具保状证为良民者,不得以竿掷城外,免于斧钺,复死于倾跌。而里巷中晓行者,暮行者,与夫行城下者,不问何人,胥用鸟枪击毙草莽无算。”[3]42由于军政当局疏散城中百姓的措施不利,镇江城内一部分士绅、百姓未能及时外逃,遭受兵燹之灾,兼之旗兵在搜捕汉奸过程中错误地伤害了一些无辜平民,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海龄的指责胜过赞扬,“但战争是残酷的,从战争的要求看这些措施实无可厚非。”[4]98-99
3. 抢掠横行,土匪肆无忌惮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英舰抵达圌山,镇江府城四门关闭,市民惊惧,纷纷罢市。“奸民以城闭,法令不行,遂聚众抢掠,各店铺米谷,所至一空。城内外一日数十起。”初九日,提督刘永孝在西门外驻地对抢掠者以军法从事,公开处决抢劫暴徒一人,一人被割去耳朵,而镇江城内“民愈乱,抢掠公行。”初十日,“南门外犹抢掠不已,兵备道与县令驻都天庙,奉提督令斩一人,鞭朴数人,奸民乃少戢。”[3]77 十四日,镇江城破,城中文武官员或死或逃,镇江陷入权力真空之中,社会失序,奸民与英夷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居民导夷鬼劫掠,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夷鬼止取金银,衣服等物件,悉归导者。导者多其家之邻友亲族与夫豢养仆人。十七日,伪提督出示禁劫掠,而劫掠如故。四乡男妇闻风亦至,土匪十倍于夷 。夷鬼止烧官房,而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重垣峻宇,尽成瓦砾场,皆土匪所为。初放火时,夷目曾缚十五人于观音庵大树上,鞭背流血,而纵火如故,夷亦无法可施。惟言经过数省,人心之坏,未有如此郡者。”[3]44-45更为可恶的是,乡下奸民闻知镇江城内抢掠成风,也趁火打劫,结伙入城参与抢劫:“廿四日,越河大港乡民二千蜂拥入城,持械抢掠,势不可挡。”[3]45英军的炮火轰击,兼之英军与土匪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使古城镇江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被占各城中损失最大、百姓处境最惨的中国城市。
三、酿成镇城治安灾难的根源
1. 政治腐败,官不履职
清朝统治阶级目光短浅,孤陋寡闻,对近代战争一无所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英军攻占宁波,两江总督裕谦投水殉节,江南震动。在扬州,士绅集资募勇,积极防御。路过扬州的新任福建汀漳龙道张集馨不以为意:“余思英夷在浙,距扬尚远,乡人胆薄,先自张皇。须知英舟笨重,内河断不能至。且英人所恃者惟舟,舍舟便无伎俩,何必纷纭杂沓,议守议迁?”[9]58当英舰抵达上海,马上溯江而上时,镇江副都统海龄更是虚张声势狂妄自大:认为夷船断不能驶入,即使英舰驶入,则“本副都统立即提兵出击,已有制胜奇策,尔民无得摇惑迁徙”。[3]75千百年来沉浸在天朝上国虚荣幻想中的封建官僚们闭目塞听,夜郎自大,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因而备战不足,最终导致丧师失地,城破民伤的严重战争灾难。
战前,文武官员议战议守,动摇不定,准备不充分,在英舰抵达镇江下游圌山时,“连日都统连府县各令宅眷出城逃去。”[3]76当英军围城,饥民无处买米,面临困境,部分知识分子勇敢担当责任,监生吴学增申请将城西门外他家400担米运进城中救济饥民时,郡守祥麟转请副都统,仍不开城,海龄以“开城吾辈命即休,不能顾百姓,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相回应,可见海龄把守住镇江城市、保证旗兵旗人生命作为第一要务,而把广大市民的生死置之度外,民之不存,要城何用?
战后,对于叛国投敌的汉奸,《江宁条约》明文规定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10]32以此之故两江总督张贴公文“榜谕汉奸,大意谓既往不咎,有控告者反坐。”[3]51百姓对此疑惑不解尚且有情可原,对于镇江陷落前后公开抢劫的违法犯罪分子,清律明文规定给予严惩:“凡强盗已行……但得事主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强盗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并积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随即奏请审决枭示。”[6]377-378法律虽有明文规定,政府居然敷衍了事,并不实力追究:“居民回城,知家中为某某所掠,不胜其愤,或鸣官指控,大宪亦多委干员办理,干员率多措置任意,听差役上下,于是差役至被告家夺其赃物,又至原告家讹诈,残灰遗瀋,扫地无余,于是民复有怨恨致死者,而差之富横如旧焉。”[3]73官员渎职、胥吏枉法导致政治腐败,可谓积重难返。
2. 民族矛盾尖锐,相互仇视
满官与汉官之间矛盾重重。虽然清政府一再表示满汉一家,不分畛域,但是,终清一代,满汉民族矛盾始终是十分尖锐的,这也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排满”口号作号召的重要原因。在镇江保卫战中,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更是显而易见:“闭城之先,副都统即疑满城皆是汉奸,日抓数人送邑令提讯,邑令钱燕桂讯明释放,即指钱令为汉奸,乘其出城,闭门不纳。城中守土官惟知府一人,与副都统为姻娅,听其所为,无能阻止。”[3]42当城中百姓缺少米粮,在城孝廉诸生十多人至知府衙门为饥民请命,请知府向副都统海龄商议,“太守不肯复与都统言,众乃太息而归。”[3]43汉民对满民也充满敌视。海龄的错误加速了镇江城市陷落的进程,百姓处境悲惨:“夷鬼沓来,不移时,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未死者多被拥抱而去,生死离散,目不忍睹。”部分汉民将对旗兵的愤怒转嫁到在城旗民的身上:“旗营中亦有未及出城者,叩户乞留,家家譟逐,无已跳入空宅中,坠厕箐,触树石者甚多,匿久则多饿死承尘土檐溜间。其妇女不能逾垣,又难匿迹,每伏池内,大半溺死,或出水潜逃,浮萍占满面上,望之如蓝面鬼然。”[3]43
汉民痛恨回民抢劫。时人认为不论城民乡民,肆意抢劫“固属同恶,而首恶犹在回民。白布裹头,持刀入人家,千百成群,所得金帛充栋,并衢巷亦为之满塞,前后巷口,不许民人出入,意犹未足。”[3]47回民甚至追踪逃难富户,假托为其看护家园,肆意勒索巨款,富户不从,则立毁坏其宅第,目无法纪,莫此为甚。汉满回民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动乱,危害社会的安定与民族的团结。
3. 道德沦丧,自相残害
镇江是座大爱之城,镇江百姓具有怜贫惜孤的优良传统:“镇江之民,一逢旱涝之灾,虽家近中人之产,无不捐赈,动以一二十万金为常,而平时有育婴、恤嫠、留养、救生、施药、施棺,以及给寒衣,散年钱储善举,无微不至,富家出资,寒士亦多出力,桑梓之情已至厚”,但镇江陷落前后,城乡奸民乘机抢劫,“力不能移之物,亦不肯留,必断碎烧毁而后去,若宿愿甚深者,人无心肝,至此已极。”[3]47 《江宁条约》签订后,居民返回城中家园,满目苍凉,遍地瓦砾,恰似人间地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夷抢掠之后,百里之内土匪结伙成百上千,执掌武器,入城搜刮,钱财衣物扫地净尽,妄顾礼仪,灭绝人伦:“其叔占侄资,甥掘舅藏,比比皆是。属离道绝,人貌兽心,吾郡祸其犹未艾乎?”[3]72读书之人参与抢劫者所在多有,士之劣者,本无为恶之才,也“穿壁逾墙,无所不至。昨丹阳令始捕一冯姓老诸生,赃至数千,法当斩,恨漏网者尚多耳。”[3]47镇江东码头一张姓生员,“至夷船报机密事,言议和是诱计,大兵已将至矣。夷首赏番银四百”,该生还与另外两名生员到丹阳,假托英夷索要军需物品,勒索丹阳县令准备大批物资解送镇江,后因其阴谋暴露而潜逃,对此,时人慨叹:“士习之坏,为古所未有。此三者实镇城之豺虎蛇蝎。”[3]47更为令人气愤的是,有些读书知礼的文化人也叛国投敌甘做汉奸:“有一诸生赴府署上书,为夷所摈。又有诸生二十多人,具牒乞充里长,伪提督坐鼓楼下亲给执照,分持而去。”[3]45
在镇江保卫战中,清军武官不能统筹全局、坚守城池,文官不能维护治安、疏散民众,城乡奸民乘机肆意烧杀抢掠,士人不能表率乡里却投敌叛国,乘机抢掠,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镇城失陷,理所当然,故时人愤怒慨叹:“镇城经此番蹂躏,破碎不堪,非夷人破碎之,镇人自破碎之也。”[3]46
战争时期的城市社会治安迥异于和平时期的社会治安,是非常态下的社会治安。军政当局在不能将百姓纳入战时体制、实现全民皆兵共赴国难的情况下,应该未雨绸缪,及时疏散百姓出城,尽量减少百姓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各级官吏亦需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切实维护战时社会稳定,最大限度确保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这就是镇江保卫战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3)[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4]严其林.镇江之战中的海龄[J].军事历史研究,2003(1):98-99.
[5]梁廷枬.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田涛,郑秦.大清律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7]许进,徐苏.陈庆年文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 :39.
[8]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四)[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9]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58.
[1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M].北京:三联书店,1957:32.
(作者为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副教授)
- 上一篇:博学多长话刘鹗
- 下一篇:晚清三状元翁同龢、王仁堪、张謇交游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