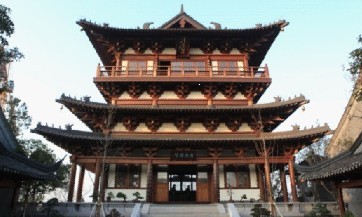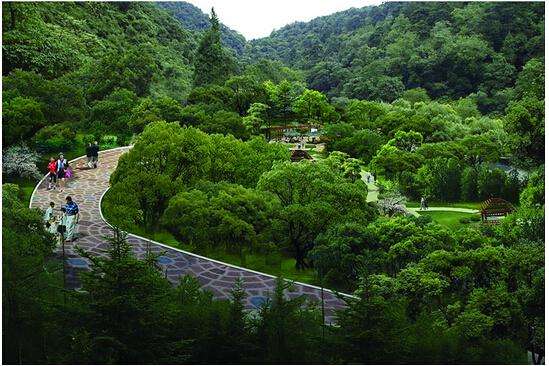走进研究会
图文推荐
试论隋代大运河开凿对镇江城市发展的贡献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18-06-15 阅读数:
试论隋代大运河开凿对镇江城市发展的贡献
吴晓峰
隋唐五代宋元几代,可以看作是镇江历史文化发展的繁荣期。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掉南朝最后一个政权——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使中国重新获得统一。据《隋书》等史料记载,隋初统治者对于刚刚武力征服的今镇江所在的陈朝旧地江南一带采取了十分强硬的压制政策,“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 更于石头置蒋州”① “这一时期,作为六朝政权核心区域的江南,在政治、文化上受到了刻意的抑制。”②是对当时江南政局的真实描述。
这种压制,通过对今镇江所在地域行政区划的改革政策上明显体现出来。“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淮南犹为徐州。后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兗。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兗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兗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兗、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南朝梁沈约《宋书·志第二十五·州郡一·南徐州》)由此可知,东晋时期,由于在京口、丹徒、曲阿沿江一带的流民多来自原徐州地区,为方便管理这些侨民,东晋政府侨置徐州、兖州等州郡,到南朝宋又改设南徐州,治所设在京口,以南徐州命名是为了与设在长江北面的徐州相区别。显然,由于南朝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及齐、梁朝皇族都来自于徐州,所以对于南徐州所辖境内格外优待。然而到了隋朝,隋文帝首先就将南徐州等侨置州郡县彻底取消清除,重新进行了统一规划。《隋书·帝纪三·炀帝上》:“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隋初对今镇江所在江南地区的强制管控,显然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隋文帝在平定了江南叛乱以后,任命杨广为扬州大总管,坐镇扬州总理江淮军政事务。自杨广总管扬州直到登上帝位以后,他改变了原来的压制政策,开始了对江南的怀柔,“杨广对江淮相对温和的政策,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执政理念,同时也与他个人喜爱南朝文化,迷恋江淮风光有关。这些因素,影响到了即位以后的杨广(隋炀帝),其开凿大运河,建江都宫,三幸扬州,这些为历代史家诟病的‘荒淫无道’之举,事实上对隋唐时期今江苏省域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③这个结论还是比较中肯的。
正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对江淮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交通便利,加上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这一带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特别是作为江河交汇处的润州,是沟通南北航运的枢纽,不仅全国各地的文人、学者、官员、商贾往来交通不绝,而且这里也是唐代以后漕运的咽喉和重要的粮食、盐、铁等货物的集散地,更是通过长江入海的海上交流往来的重要出入口,这种特殊的地域资源优势为镇江在后世的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确定了镇江在隋至元代历史文化的繁荣。
一、江南运河的穿凿与镇江城市功能嬗变
据史料记载,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废北周静帝,自立为帝,建立了隋朝。当时的都城仍在汉代的长安古城。然而这座旧城,历经近800年的沧桑,不仅宫室破败城区狭小,且因供水、排水不畅,水污染严重等问题,已经不再适合新的统一大帝国的需要,因此,隋文帝杨坚决定另建新的都城,这就是由宇文恺负责建造的大兴城(唐朝建立后更名为长安城,今陕西西安)。隋文帝定都大兴城以后为了方便转运各地的粮食来供应大兴城,于开皇四年(584年)下令开通了广通渠,沟通了从潼关至大兴城的漕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又从大兴城与洛阳的地理位置考虑,决定将国家政权的中心由关中向东迁移,于大业元年(605)三月,正式启动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因为大兴城地处关中,与外界交通不便,所谓“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隋书》卷3《炀帝纪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洛阳自古就有“天下之中”之称,《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故《隋书·炀帝纪》记载了杨广当时下达的诏书说:“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具有“控以三河(黄河、洛河、涧河的交汇之地),固以四塞,水路通,供赋等”等优势。以洛阳这样的地理位置,在这里建都,确实适合统一大帝国统治的需要。
随着洛阳都城的落成,隋炀帝又发动开凿大运河工程:(1)大业元年(605)三月,调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黄河。又自板诸(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历荥泽入汴水;又自开封之东引汴入泗,达于淮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通邗沟(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经江都(扬州)至扬子入江。(2)大业四年(608),“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3)大业六年(610)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高祖文皇帝下》;《隋纪》五《炀皇帝上之下》)。这三项工程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就形成以江南运河、邗沟与通济渠、永济渠、广通渠为主体的多枝形运河系统,沟通了钱塘江和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联系,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呈扇形分布的水上交通枢纽,其中沟通我国东南地区与长江、淮河直至都城洛阳的江南河段就是从镇江开始起航的。
清人顾祖禹引《江防考》所言:“京口西接石头(今南京),东至大海,北距广陵,而金、焦障其中流,实天设之险。繇京口抵石头凡二百里,高冈逼岸,宛如长城,未易登犯。繇京口而东至孟渎七十余里,或高峰横亘,或江泥沙淖,或洲渚错列,所谓二十八港者皆浅涩短狭,难以通行。故江岸之防惟在京口,而江中置防则圌山为最要。”①应是对镇江当时地理条件的真实概括。由于长江横绝与京口天然的地理优势,决定了古代镇江是北方中原与江南交流的唯一出口,所以,在六朝,京口是京城建康的门户,是沟通京城与外界的咽喉要道,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而如今随着江南运河的开凿,镇江就成为连接长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然而,由于隋末的动乱和隋朝的短命,运河巨大而长远的功能在当时并没有显示出来,甚至被看做是隋炀帝杨广奢侈残暴的罪证。“从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看,炀帝在位时及唐代前期,几乎没有人说过开运河的好话,往往将之视为炀帝身死人手、隋朝短命亡国的重要原因。
但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论调为之一变。尽管也还有人在批评炀帝的劳民伤财,但毕竟有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运河的意义了。①唐代中期以后,北方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九十一),社会经济极其匮乏,朝廷府库空虚。而江淮以南,已经东晋、南朝以来300多年的开发,社会经济本就优越于北方,又没有受到太多北方动乱的影响,因此,得以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物产资源丰富。自中唐起,江南就成为唐朝赋税和漕粮最主要的供应地。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列传》第九十)韩愈也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②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亦曾言:“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力焉。”③
可见,自中唐以后,由于江南是全国经济的重心,而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洛阳则在北方中原,山河重阻,陆路运输异常艰难,为了满足首都对江南经济的需求,大运河的作用就越发凸显出来,特别是为了保证江南财富对中原的供应,保证江南运河的畅通也成了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唐、宋以来历届朝廷都对江南运河不遗余力地经营,也因而促进了镇江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
许辉先生的《江苏境内唐宋运河的变迁及其历史作用》将江南运河分为北段、中段和南段三个部分:其中北段从镇江出发至望亭(今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江南运河中段从望亭至平望(今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间,地势比较平缓;江南运河南段,由杭州至嘉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从运河的走向来看,镇江段是始发段,地势较高,所以保证镇江段的水源,应该是保证江南运河畅通的关键。特别是由镇江至丹阳一段,地势最高亢、又多冈陇,每到汛期,有长江水内灌,水量充足,通航就很便利,但遇长江水位低落时节,水量不足,就会影响航运。为了节制水流,维持运道水深,以利转漕,历代都有关于兴修南北两端堰(埭)闸和疏浚练湖的记录,通过这些措施以控制水量,维持航运畅通。“到宋淳化(990)以前,这一河段运河上已设有京口、吕城、奔牛、望亭等4堰,分级蓄水,维持通航……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对练湖的疏浚更为频繁”④ 。另外,在唐代开元年间,由于运河镇江段的长江入水口在京口埭,官府又于扬州南瓜洲浦开凿了伊娄运河,由镇江开往扬州的船只通过伊娄运河直达北岸,大大缩短了镇江与扬州之间的航运距离。也使京口的航运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其作为江河要津的地位更加加强。
经过历代对于江南运河的治理,形成了以镇江为中心,长江横贯东西、运河竖穿南北的十字黄金水道,确定了镇江作为江河要津的历史地位。在由唐至元的几代,镇江始终扮演着贯通南北连接东西航运的交通枢纽的重要角色。江南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经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北方的中原文化资源也经由这里引进到了江南,位于长江和江南运河交接点上的镇江,是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直接窗口和中转站,是南北经济文化的传输点,也是保证江南运河畅通无阻的重要关口,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因而确立了镇江在唐、宋、元时期极其特殊的城市地位。
二、 大运河带动隋唐五代与宋元镇江城市的发展与兴盛
“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这段记载描述的是隋代镇江的自然状况,也反映出作为军事重镇特有的民风。然而,随着江南运河的通航,镇江作为江河要津的地位日益巩固,其城市地位也得到了不断地提高。由六朝军事重镇为主转变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通枢纽和南北货物的集散地。这种城市地位的转变,从隋前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中得到证实。
据《汉书》,镇江在汉代为丹徒县,属会稽郡管辖。三国吴时建京口,其城市地位初步得到提高。东晋以后在此置南徐州,其城市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隋平陈,因废南徐州以为延陵镇,移居于京口,为延陵县,属蒋州。开皇十五年(595),罢延陵镇,以蒋州之延陵、永年、常州之曲阿三县置润州于镇城,盖取州东润浦以立名焉。大业三年(607),废江都郡之延陵县为丹徒,徙延陵还治故县,属茅州。六年(610),辅公祏反,复据其地。七年(611),贼平。又置润州,领丹徒县。八年(612),废润州以曲阿来属。九年(613),扬州移理江都,以延陵、句容、白下三县属润州。天宝元年(742),改为丹阳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润州。永泰(765-766)后,常为浙西道观察使理所。皇朝为镇江军节度。”(《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九《江南东道》一《润州》)可见,随着江南运河地位的凸显,镇江自唐代中期以后城市地位也越来越巩固提高,不仅由古代的丹徒县上升为州、府所在地,而且在唐及两宋时期,始终处于控制浙西咽喉的地位。且宋开宝八年(975年)起,改唐时所置镇海军节度使为镇江军节度使,政和三年(1113年),改润州为镇江府,镇江之名自此始。“唐之中叶,以镇海为重镇,浙西安危,系于润州。宋南渡以后,常驻重军于此,以控江口。”①及至元代,镇江的城市地位仍有提高。“至元十三年(1276),升为镇江路,戸一十万三千三百一十五,口六十二万三千六百四十四。领司一、县三:录事司,县三:丹徒、丹阳、金坛。”②
可见,自唐至元,镇江的城市地位始终处于上升和发展的趋势。而这种上升的主要原因与其处于南北交通枢纽的地位息息相关。宋人吕祖谦曾云:“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陜西到长安是一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所谓无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并会于京口,京口是诸侯咽喉处。初时润州,江淮之粟至于京口,到得中间,河南、陜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历代制度详说》卷四《漕运》)可谓通识之论。镇江的交通枢纽地位,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繁荣。使之较早成为江南最主要的大都市之一。“承太伯之高踪,由季子之遗烈,盖英贤之旧壤,杂吴夏之语音。人性质直,黎庶淳让。言地则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举江左之郡者,常、润其首焉。”(《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江南东道》四《常州》)可见,在宋代,常州和润州是江南首屈一指的两大最主要都市,“西距汉沔,东连海峤,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①,这些评价都是有根据的。
随着运河的开通与江南经济的不断发展,南粮北运在唐代即成定制,大批漕米、土产和手工业品经镇江中转运往京都和中原,镇江无疑已成为南北漕运的咽喉所在。1971年1月发掘出土的洛阳含嘉仓160号窖遗址中出土的铭砖除记载了储粮的时间、数量、品种、来源、仓窖位置及授领粮食的官员姓名以外,还记载了所储粮食的来源,主要有苏州、徐州、楚州、润州、滁州等。②现存传世文献宋《嘉定镇江志》和元《至顺镇江志》也都记载了镇江的粮仓情况。如南宋在镇江府建大军仓作为粮食存储转运之所,绍兴七年(1137)建成,当时储米六十余万石,到嘉定甲戌(1214)年间,因郡守史弥远认为“滨江积贮,最为利济,要须储蓄百万,以便转输”,大军仓分南、西、北三所,元代改北仓为香糯仓“以受本路及常州路上供香糯”;咸淳年间(1265-1274)淮浙发运司在镇江府吕城镇设有年仓,“凡四十廒,受纳苏、常公租,转输镇江转般仓,折运过淮。后隶浙西提刑司,谓之都仓”。③除有储存转输粮食的各类粮仓以外,还有储存其他各类货物的库,如军资库、公使钱库、督醋库等等各类名目不计其数,可证镇江在漕粮等物资转运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向朝廷输送的货物种类越来越多,镇江的航运业越来越繁忙,大量的布帛、铜器、铁器、茶叶、盐、鱼等物源源不断地经镇江转运到北方,包括各地进献给朝廷的贡品也在镇江集结北运。
因此,唐、宋、元几代,镇江都是两浙乃至诸道、路漕粮集结北运的中心,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唐、宋的浙西道观察使司均设在镇江,而观察使也往往兼任江淮转运使、诸道盐铁转运使等职,“然扼江淮南北之衢,势便地顺,他州终不及”④由于镇江独到的地理位置,使它的发展远远超出其他各州,发展成为宋、元时期江南最大的都市。“润州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运河的入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独称列岳’,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注:《唐代墓志汇编》垂拱○五二(无志名);《文苑英华》卷408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润州是浙西观察使的治所,凭借了长江和江南运河而工商业发展较快。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饶。’‘碧鸡白马回翔久,却忆朱方是乐郊。’(注:《全唐诗》卷359刘禹锡《重送浙西李相公》。)”⑤这样的描述,可以视为唐代镇江乃至五代、宋、元交通运输发达、都市繁荣的真实写照。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大画家米芾曾任发运司属官,主管江淮间的水路运输事宜。因在润州定居一段时间,作有赞美镇江的诗歌,可以反映出当时镇江的江山形胜与文化的繁荣。其赞美北固山上的多景楼,诗云:“两州城郭靑烟起,千里江山白鹭飞。海近云涛惊夜梦,天低月露湿秋衣。”赞美《望江楼》诗云:“云间铁瓮近靑天,缥缈飞楼百尺连。三峡江声流笔下,六朝山影落尊前。几畨画角催红日,无事沧洲起白烟。忽忆赏心何处在,春风秋月两茫然。”到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东南一隅,江南财赋的周转与朝廷的供应等都要从镇江转输,镇江城市的地位更加重要了。既是繁忙的漕运货物集散地,又是重要的军事重镇,致使多次重大的抗金战役在此发生,也使岳飞、韩世忠、辛弃疾等抗金英雄的故事被镇江人世代相传。
漕运的发达,促进了镇江城市的繁荣,宋、元时期,镇江是江南最大的都市之一。据元《至顺镇江志》记载,当时的镇江人口众多,超过了以前各代。“润为东南重镇,晋、宋、隋、唐,地大民鲜。至宋嘉定间(1208-1224),所统唯三县,而户口之繁,视前代为最。北南混一,兹郡实先内附,兵不血刃,市不辍肆。故至元庚寅(1290),籍民之数与嘉定等。”(《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也就是说,作为东南重镇的镇江,从晋代至唐代以来都是以地大民稀著称的,但是到南宋嘉定年间达到繁荣阶段,人口一度居于前代之最,而南宋灭亡以来,由于镇江当地首先主动归附了元军,所以当地经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甚至市场上的商贸活动都正常进行而没有停止。大量的人口带动了市场的繁荣。唐、宋至元代,镇江市场贸易充足,货物种类丰富,财税充盈。既有官营的商业活动,也有民间自发的商业活动。“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曰市矣,则有市道焉。相时之宜,以懋迁其有无,揣人情之缓急,而上下其物……此固市道之常。”(《漫塘集》巻二十三《记丁桥太霄观记》)这是对当时民间贸易活动的真实记录。唐代以来,专门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业集市称为坊或市。宋、元两代,镇江大大小小的商业集市非常多。元代镇江路仅录事司所辖坊就有二十八家,市五家:大市、小市、马市、米市、菜市;丹徒县有酒坊三十四,丹阳县有酒坊五十五,当时镇江酒业发达,酒的贸易也最繁荣。其他各种专业坊亦不胜枚举。商业发达,故而税收事务繁忙。宋、元两代官府在镇江设置很多负责商贸、运输等事务的机构,称为“务”,《至顺镇江志》中提到镇江路的商税部门:“本府:比较东务、贡罗务、在城务;丹徒县:比较西务、谏壁务、丁角务;丹阳县:延陵税务、延陵酒务、吕城务、吕城酒务、丹阳务、酒务;金坛县:酒务、金坛务”①等,说明元代的镇江路继续保持了宋代镇江商业繁荣的特色。
(作者为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
吴晓峰
隋唐五代宋元几代,可以看作是镇江历史文化发展的繁荣期。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掉南朝最后一个政权——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使中国重新获得统一。据《隋书》等史料记载,隋初统治者对于刚刚武力征服的今镇江所在的陈朝旧地江南一带采取了十分强硬的压制政策,“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 更于石头置蒋州”① “这一时期,作为六朝政权核心区域的江南,在政治、文化上受到了刻意的抑制。”②是对当时江南政局的真实描述。
这种压制,通过对今镇江所在地域行政区划的改革政策上明显体现出来。“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淮南犹为徐州。后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兗。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兗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兗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兗、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南朝梁沈约《宋书·志第二十五·州郡一·南徐州》)由此可知,东晋时期,由于在京口、丹徒、曲阿沿江一带的流民多来自原徐州地区,为方便管理这些侨民,东晋政府侨置徐州、兖州等州郡,到南朝宋又改设南徐州,治所设在京口,以南徐州命名是为了与设在长江北面的徐州相区别。显然,由于南朝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及齐、梁朝皇族都来自于徐州,所以对于南徐州所辖境内格外优待。然而到了隋朝,隋文帝首先就将南徐州等侨置州郡县彻底取消清除,重新进行了统一规划。《隋书·帝纪三·炀帝上》:“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隋初对今镇江所在江南地区的强制管控,显然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隋文帝在平定了江南叛乱以后,任命杨广为扬州大总管,坐镇扬州总理江淮军政事务。自杨广总管扬州直到登上帝位以后,他改变了原来的压制政策,开始了对江南的怀柔,“杨广对江淮相对温和的政策,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执政理念,同时也与他个人喜爱南朝文化,迷恋江淮风光有关。这些因素,影响到了即位以后的杨广(隋炀帝),其开凿大运河,建江都宫,三幸扬州,这些为历代史家诟病的‘荒淫无道’之举,事实上对隋唐时期今江苏省域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③这个结论还是比较中肯的。
正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对江淮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交通便利,加上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这一带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特别是作为江河交汇处的润州,是沟通南北航运的枢纽,不仅全国各地的文人、学者、官员、商贾往来交通不绝,而且这里也是唐代以后漕运的咽喉和重要的粮食、盐、铁等货物的集散地,更是通过长江入海的海上交流往来的重要出入口,这种特殊的地域资源优势为镇江在后世的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确定了镇江在隋至元代历史文化的繁荣。
一、江南运河的穿凿与镇江城市功能嬗变
据史料记载,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废北周静帝,自立为帝,建立了隋朝。当时的都城仍在汉代的长安古城。然而这座旧城,历经近800年的沧桑,不仅宫室破败城区狭小,且因供水、排水不畅,水污染严重等问题,已经不再适合新的统一大帝国的需要,因此,隋文帝杨坚决定另建新的都城,这就是由宇文恺负责建造的大兴城(唐朝建立后更名为长安城,今陕西西安)。隋文帝定都大兴城以后为了方便转运各地的粮食来供应大兴城,于开皇四年(584年)下令开通了广通渠,沟通了从潼关至大兴城的漕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又从大兴城与洛阳的地理位置考虑,决定将国家政权的中心由关中向东迁移,于大业元年(605)三月,正式启动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因为大兴城地处关中,与外界交通不便,所谓“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隋书》卷3《炀帝纪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洛阳自古就有“天下之中”之称,《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故《隋书·炀帝纪》记载了杨广当时下达的诏书说:“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具有“控以三河(黄河、洛河、涧河的交汇之地),固以四塞,水路通,供赋等”等优势。以洛阳这样的地理位置,在这里建都,确实适合统一大帝国统治的需要。
随着洛阳都城的落成,隋炀帝又发动开凿大运河工程:(1)大业元年(605)三月,调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黄河。又自板诸(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历荥泽入汴水;又自开封之东引汴入泗,达于淮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通邗沟(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经江都(扬州)至扬子入江。(2)大业四年(608),“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3)大业六年(610)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高祖文皇帝下》;《隋纪》五《炀皇帝上之下》)。这三项工程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就形成以江南运河、邗沟与通济渠、永济渠、广通渠为主体的多枝形运河系统,沟通了钱塘江和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联系,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呈扇形分布的水上交通枢纽,其中沟通我国东南地区与长江、淮河直至都城洛阳的江南河段就是从镇江开始起航的。
清人顾祖禹引《江防考》所言:“京口西接石头(今南京),东至大海,北距广陵,而金、焦障其中流,实天设之险。繇京口抵石头凡二百里,高冈逼岸,宛如长城,未易登犯。繇京口而东至孟渎七十余里,或高峰横亘,或江泥沙淖,或洲渚错列,所谓二十八港者皆浅涩短狭,难以通行。故江岸之防惟在京口,而江中置防则圌山为最要。”①应是对镇江当时地理条件的真实概括。由于长江横绝与京口天然的地理优势,决定了古代镇江是北方中原与江南交流的唯一出口,所以,在六朝,京口是京城建康的门户,是沟通京城与外界的咽喉要道,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而如今随着江南运河的开凿,镇江就成为连接长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然而,由于隋末的动乱和隋朝的短命,运河巨大而长远的功能在当时并没有显示出来,甚至被看做是隋炀帝杨广奢侈残暴的罪证。“从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看,炀帝在位时及唐代前期,几乎没有人说过开运河的好话,往往将之视为炀帝身死人手、隋朝短命亡国的重要原因。
但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论调为之一变。尽管也还有人在批评炀帝的劳民伤财,但毕竟有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运河的意义了。①唐代中期以后,北方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九十一),社会经济极其匮乏,朝廷府库空虚。而江淮以南,已经东晋、南朝以来300多年的开发,社会经济本就优越于北方,又没有受到太多北方动乱的影响,因此,得以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物产资源丰富。自中唐起,江南就成为唐朝赋税和漕粮最主要的供应地。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列传》第九十)韩愈也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②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亦曾言:“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力焉。”③
可见,自中唐以后,由于江南是全国经济的重心,而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洛阳则在北方中原,山河重阻,陆路运输异常艰难,为了满足首都对江南经济的需求,大运河的作用就越发凸显出来,特别是为了保证江南财富对中原的供应,保证江南运河的畅通也成了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唐、宋以来历届朝廷都对江南运河不遗余力地经营,也因而促进了镇江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
许辉先生的《江苏境内唐宋运河的变迁及其历史作用》将江南运河分为北段、中段和南段三个部分:其中北段从镇江出发至望亭(今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江南运河中段从望亭至平望(今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间,地势比较平缓;江南运河南段,由杭州至嘉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从运河的走向来看,镇江段是始发段,地势较高,所以保证镇江段的水源,应该是保证江南运河畅通的关键。特别是由镇江至丹阳一段,地势最高亢、又多冈陇,每到汛期,有长江水内灌,水量充足,通航就很便利,但遇长江水位低落时节,水量不足,就会影响航运。为了节制水流,维持运道水深,以利转漕,历代都有关于兴修南北两端堰(埭)闸和疏浚练湖的记录,通过这些措施以控制水量,维持航运畅通。“到宋淳化(990)以前,这一河段运河上已设有京口、吕城、奔牛、望亭等4堰,分级蓄水,维持通航……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对练湖的疏浚更为频繁”④ 。另外,在唐代开元年间,由于运河镇江段的长江入水口在京口埭,官府又于扬州南瓜洲浦开凿了伊娄运河,由镇江开往扬州的船只通过伊娄运河直达北岸,大大缩短了镇江与扬州之间的航运距离。也使京口的航运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其作为江河要津的地位更加加强。
经过历代对于江南运河的治理,形成了以镇江为中心,长江横贯东西、运河竖穿南北的十字黄金水道,确定了镇江作为江河要津的历史地位。在由唐至元的几代,镇江始终扮演着贯通南北连接东西航运的交通枢纽的重要角色。江南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经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北方的中原文化资源也经由这里引进到了江南,位于长江和江南运河交接点上的镇江,是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直接窗口和中转站,是南北经济文化的传输点,也是保证江南运河畅通无阻的重要关口,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因而确立了镇江在唐、宋、元时期极其特殊的城市地位。
二、 大运河带动隋唐五代与宋元镇江城市的发展与兴盛
“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这段记载描述的是隋代镇江的自然状况,也反映出作为军事重镇特有的民风。然而,随着江南运河的通航,镇江作为江河要津的地位日益巩固,其城市地位也得到了不断地提高。由六朝军事重镇为主转变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通枢纽和南北货物的集散地。这种城市地位的转变,从隋前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中得到证实。
据《汉书》,镇江在汉代为丹徒县,属会稽郡管辖。三国吴时建京口,其城市地位初步得到提高。东晋以后在此置南徐州,其城市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隋平陈,因废南徐州以为延陵镇,移居于京口,为延陵县,属蒋州。开皇十五年(595),罢延陵镇,以蒋州之延陵、永年、常州之曲阿三县置润州于镇城,盖取州东润浦以立名焉。大业三年(607),废江都郡之延陵县为丹徒,徙延陵还治故县,属茅州。六年(610),辅公祏反,复据其地。七年(611),贼平。又置润州,领丹徒县。八年(612),废润州以曲阿来属。九年(613),扬州移理江都,以延陵、句容、白下三县属润州。天宝元年(742),改为丹阳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润州。永泰(765-766)后,常为浙西道观察使理所。皇朝为镇江军节度。”(《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九《江南东道》一《润州》)可见,随着江南运河地位的凸显,镇江自唐代中期以后城市地位也越来越巩固提高,不仅由古代的丹徒县上升为州、府所在地,而且在唐及两宋时期,始终处于控制浙西咽喉的地位。且宋开宝八年(975年)起,改唐时所置镇海军节度使为镇江军节度使,政和三年(1113年),改润州为镇江府,镇江之名自此始。“唐之中叶,以镇海为重镇,浙西安危,系于润州。宋南渡以后,常驻重军于此,以控江口。”①及至元代,镇江的城市地位仍有提高。“至元十三年(1276),升为镇江路,戸一十万三千三百一十五,口六十二万三千六百四十四。领司一、县三:录事司,县三:丹徒、丹阳、金坛。”②
可见,自唐至元,镇江的城市地位始终处于上升和发展的趋势。而这种上升的主要原因与其处于南北交通枢纽的地位息息相关。宋人吕祖谦曾云:“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陜西到长安是一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所谓无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并会于京口,京口是诸侯咽喉处。初时润州,江淮之粟至于京口,到得中间,河南、陜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历代制度详说》卷四《漕运》)可谓通识之论。镇江的交通枢纽地位,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繁荣。使之较早成为江南最主要的大都市之一。“承太伯之高踪,由季子之遗烈,盖英贤之旧壤,杂吴夏之语音。人性质直,黎庶淳让。言地则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举江左之郡者,常、润其首焉。”(《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江南东道》四《常州》)可见,在宋代,常州和润州是江南首屈一指的两大最主要都市,“西距汉沔,东连海峤,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①,这些评价都是有根据的。
随着运河的开通与江南经济的不断发展,南粮北运在唐代即成定制,大批漕米、土产和手工业品经镇江中转运往京都和中原,镇江无疑已成为南北漕运的咽喉所在。1971年1月发掘出土的洛阳含嘉仓160号窖遗址中出土的铭砖除记载了储粮的时间、数量、品种、来源、仓窖位置及授领粮食的官员姓名以外,还记载了所储粮食的来源,主要有苏州、徐州、楚州、润州、滁州等。②现存传世文献宋《嘉定镇江志》和元《至顺镇江志》也都记载了镇江的粮仓情况。如南宋在镇江府建大军仓作为粮食存储转运之所,绍兴七年(1137)建成,当时储米六十余万石,到嘉定甲戌(1214)年间,因郡守史弥远认为“滨江积贮,最为利济,要须储蓄百万,以便转输”,大军仓分南、西、北三所,元代改北仓为香糯仓“以受本路及常州路上供香糯”;咸淳年间(1265-1274)淮浙发运司在镇江府吕城镇设有年仓,“凡四十廒,受纳苏、常公租,转输镇江转般仓,折运过淮。后隶浙西提刑司,谓之都仓”。③除有储存转输粮食的各类粮仓以外,还有储存其他各类货物的库,如军资库、公使钱库、督醋库等等各类名目不计其数,可证镇江在漕粮等物资转运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向朝廷输送的货物种类越来越多,镇江的航运业越来越繁忙,大量的布帛、铜器、铁器、茶叶、盐、鱼等物源源不断地经镇江转运到北方,包括各地进献给朝廷的贡品也在镇江集结北运。
因此,唐、宋、元几代,镇江都是两浙乃至诸道、路漕粮集结北运的中心,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唐、宋的浙西道观察使司均设在镇江,而观察使也往往兼任江淮转运使、诸道盐铁转运使等职,“然扼江淮南北之衢,势便地顺,他州终不及”④由于镇江独到的地理位置,使它的发展远远超出其他各州,发展成为宋、元时期江南最大的都市。“润州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运河的入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独称列岳’,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注:《唐代墓志汇编》垂拱○五二(无志名);《文苑英华》卷408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润州是浙西观察使的治所,凭借了长江和江南运河而工商业发展较快。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饶。’‘碧鸡白马回翔久,却忆朱方是乐郊。’(注:《全唐诗》卷359刘禹锡《重送浙西李相公》。)”⑤这样的描述,可以视为唐代镇江乃至五代、宋、元交通运输发达、都市繁荣的真实写照。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大画家米芾曾任发运司属官,主管江淮间的水路运输事宜。因在润州定居一段时间,作有赞美镇江的诗歌,可以反映出当时镇江的江山形胜与文化的繁荣。其赞美北固山上的多景楼,诗云:“两州城郭靑烟起,千里江山白鹭飞。海近云涛惊夜梦,天低月露湿秋衣。”赞美《望江楼》诗云:“云间铁瓮近靑天,缥缈飞楼百尺连。三峡江声流笔下,六朝山影落尊前。几畨画角催红日,无事沧洲起白烟。忽忆赏心何处在,春风秋月两茫然。”到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东南一隅,江南财赋的周转与朝廷的供应等都要从镇江转输,镇江城市的地位更加重要了。既是繁忙的漕运货物集散地,又是重要的军事重镇,致使多次重大的抗金战役在此发生,也使岳飞、韩世忠、辛弃疾等抗金英雄的故事被镇江人世代相传。
漕运的发达,促进了镇江城市的繁荣,宋、元时期,镇江是江南最大的都市之一。据元《至顺镇江志》记载,当时的镇江人口众多,超过了以前各代。“润为东南重镇,晋、宋、隋、唐,地大民鲜。至宋嘉定间(1208-1224),所统唯三县,而户口之繁,视前代为最。北南混一,兹郡实先内附,兵不血刃,市不辍肆。故至元庚寅(1290),籍民之数与嘉定等。”(《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也就是说,作为东南重镇的镇江,从晋代至唐代以来都是以地大民稀著称的,但是到南宋嘉定年间达到繁荣阶段,人口一度居于前代之最,而南宋灭亡以来,由于镇江当地首先主动归附了元军,所以当地经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甚至市场上的商贸活动都正常进行而没有停止。大量的人口带动了市场的繁荣。唐、宋至元代,镇江市场贸易充足,货物种类丰富,财税充盈。既有官营的商业活动,也有民间自发的商业活动。“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曰市矣,则有市道焉。相时之宜,以懋迁其有无,揣人情之缓急,而上下其物……此固市道之常。”(《漫塘集》巻二十三《记丁桥太霄观记》)这是对当时民间贸易活动的真实记录。唐代以来,专门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业集市称为坊或市。宋、元两代,镇江大大小小的商业集市非常多。元代镇江路仅录事司所辖坊就有二十八家,市五家:大市、小市、马市、米市、菜市;丹徒县有酒坊三十四,丹阳县有酒坊五十五,当时镇江酒业发达,酒的贸易也最繁荣。其他各种专业坊亦不胜枚举。商业发达,故而税收事务繁忙。宋、元两代官府在镇江设置很多负责商贸、运输等事务的机构,称为“务”,《至顺镇江志》中提到镇江路的商税部门:“本府:比较东务、贡罗务、在城务;丹徒县:比较西务、谏壁务、丁角务;丹阳县:延陵税务、延陵酒务、吕城务、吕城酒务、丹阳务、酒务;金坛县:酒务、金坛务”①等,说明元代的镇江路继续保持了宋代镇江商业繁荣的特色。
(作者为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
- 上一篇:试析吕凤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下一篇:京口柳氏宗族家训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