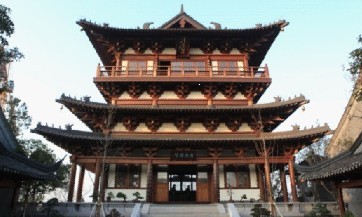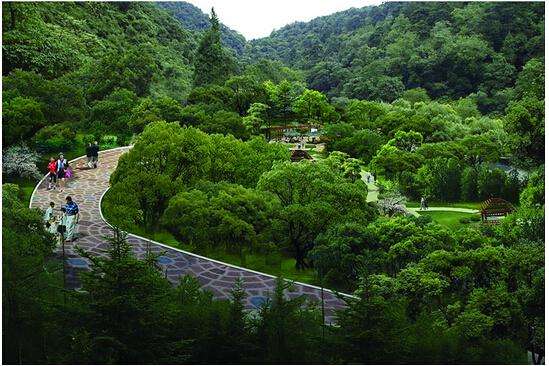走进研究会
图文推荐
“啷当”和“丹剧”之间的脉络形态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24-12-20 阅读数:
“啷当”和“丹剧”之间的脉络形态
罗戎平
“啷”,在《辞海》中释义为“象声”字;“当”,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可作为“助动词”,在“百度汉语”里将其合并,解释为:“啷当(丹剧的原身)”。
“啷当”,俗称“啷当说唱”,全称“瞽目啷当”。“瞽目”,即失明者,也就是失明者表演的“啷当说唱”,它是自清代中晚期流传于江苏丹阳、金坛、丹徒和武进等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形式。说唱者,旧时多为年轻的盲女。清代黄周星撰写的曲论《制曲枝语》和昭梿著笔记《啸亭杂录》, 还将盲词分成了三类:一是弹词,二是日间算命、夜间唱书的算命调,三是击鼓弹唱的盲词。
一、“啷当”的产生与兴起
说到“瞽目啷当”,就得谈到清嘉庆年间南京在城中设立的“瞽目院”,也就是向盲人传授常识性知识和生活技能的盲校,只不过该“瞽目院”在道光末年解体,盲人各奔东西,前往东南方向的除少数流向浙江外,大部分都落脚在江苏丹阳、金坛、丹徒等地,以沿门说唱维持生计。丹阳的“瞽目啷当”兴起于清道光年间,至光绪年尤为盛行,说唱之风强盛,丹阳各乡镇的茶馆、书场、晒场、庙堂、庭院等场所,处处都闻“啷当”之声,“黄秧下田谷进仓,麦场头里笃啷当”的丹阳民谣,足以反映出当年之风行。
若论及这种说唱的渊源可前溯至南宋诗人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中写下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的诗句,它说的是夕阳时分,击鼓传唱的盲眼老翁正在演出的情景。如此看来,这瞽目说唱至少也有800 年的历史。
丹阳啷当,以丹阳一带的牛郎调、佛祈调、油嘴调、梅花调等民歌为基础,以丹阳方言为依托,曲调优美朴实,乡土味浓,其特点为“说唱结合,以唱为主;在单口、对口、群口、走唱、坐唱中,以单口坐唱为主。”
啷当唱腔统称“啷当调”,其完整的唱腔系列是由吟板、正板、行板、数板、急板、凳板、叫板等十多种板式组成,演唱者按曲目内容和表演需要确定板式,每种板式都有固定的竹板和竹鼓敲击“板头”导入唱腔,曲目内容多为戏曲故事和民间传奇,但不说唱史书。
在说唱乐器上,最初使用的是书弦和皮鼓,因当时市场紧俏,遂以竹板和竹鼓代之,而后的表演形式也由走唱改为了以坐唱为主。在说唱方法上,主要有叙述性唱腔,特点是行腔平稳,以婉转细腻见长;情绪性唱腔,特点是行腔激越,以强弱有致称绝。在竹鼓演奏上,有“的笃滚弹”等诸法,具体表现为“全击、间击、点击”等数种。
虽然“瞽目啷当”中的说唱者大多为年轻盲女,但不论男女只要入行,都会被人尊称为“先生”,并且“女先生”一般也习惯性地戴一副墨镜,这让她们显得俊俏又精神,表演起来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每到“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四个传统节日,丹阳啷当的说唱活动最为频繁,其书目分为“滩头”和“本头”两种。“滩头”一唱到底,无道白,多为年轻盲女演唱;“本头”说唱并重,为正书,十之八九为男艺人。流行的“滩头”曲目有《白蛇精》《夸新妇》《十羞君王》《送子入学》等几十部;流行的“本头”曲目有《红粉记》《琵琶记》《青楼记》《牙痕记》等几十部。曲目之丰富,时有“七十二记,四十八滩头”之说。清末民初走红的十多位啷当艺人,大多是唱“滩头”的,而靠“本头”以长篇书目唱红的只有三四位,同行公认的仅李宝儿一人,她每次说唱,听客少则几百, 多则上千。和其他艺人不同的是,李宝儿(约1972-1920 年)从不走村串巷,想听她说唱,都要拿着帖子上门去请。由她说唱的《卖花记》《荆钗记》《遇仙记》《青楼记》等四部曲目,其“声”其“神”所呈现出来的生动的现场感,在雨点般的击鼓声和竹板的脆响声中,好评爆棚,一时“李四记”的艺名呼之欲出,家喻户晓,粉丝无数。
同时值得推介的还有“滩头王”刘春仙(约1850-1916 年)、“啷当名师”王雪青(1881-1938年)。
刘春仙,女,丹阳窦庄人,年过40 才开始坐唱,特别擅唱“滩头”曲目,故有“滩头王”之美称,所唱曲目有《十指骂古人名》《十二房媳妇》《二十四个孝》等,她从不收徒,因而没有唱本传世;
王雪青,女,丹阳麦溪人,自幼随母亲学习啷当,学成后在麦溪镇“王连庄啷当家班”掌门授徒,是啷当界公认的一代名师。可以想象名噪一时的“啷当王氏三姐妹”鲍莲娣、赵金花、蒋六英均出自她的门下,其传授的曲目有《小红灯》《小货郎》《芭蕉记》《长工记》等。
与此同时,也就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丹阳还出现了一批有社会影响的“瞽目啷当”传习所,当时有横塘乡八里桥英家村、陵口乡张巷村、荆林乡四巷村、前艾乡大英巷、松卜乡(今属麦溪镇)王连庄等。其中上述的“王连庄啷当家班”是家传性质的啷当女班,是丹阳啷当在同治年间开创最早的传习机构,它只收孤女为徒,并立有规矩:徒弟学成后如需授艺必须回到王连庄进行,不得另立山头。
当时的啷当说唱势头很猛,至民国十六年(1927 年),啷当艺人蒋寿寿、陈腊荣等人在丹阳西门蒋家园观音堂内开设了“丹阳啷当总传习所”,教员先后有陈腊荣、贡景春、卞扣保、王和连、刘连生等人,学员大多为盲人或半盲人,初学艺者学制三年,总传习所的具体工作由董事会负责,第一届董事长贡景春,周边城镇邻县有得知消息的,也纷纷送学员前来就学。
民国二十年(1931 年),由总传习所发起的“丹阳啷当艺人行会”成立,也称“孤老院行班”,这是啷当艺人唯一的管理机构,地点仍设在西门的蒋家园观音堂内,总会长陈腊荣。副总会长卞扣宝( 艺名柯宝),后又增补刘连生。“行会”下设十个分行,东西两路各领五行,这也就有了人们后来常说到的东路和西路啷当。
东路啷当由柯宝领班,西路啷当由刘连生领班。每行各有一人主管,称之“行头”。东路的大行负责曲目传授和行会管理,二行负责书场和堂会演出,三行管理农村庭院和场头艺人,四行管理滩头走唱艺人,五行管理艺徒实习。西路的六行至十行与东路的五行工作职责相同。各行有分工,艺人称之“五作”,即:行头作、主演作、演出作、配演作、习演作。各行均可收徒,先定师徒名分,师满后按艺人的实际水平再分配到相应的行班。
东路啷当的教员先后有:蒋寿寿、李福川、卞扣宝、夏万勤、夏万勇、王和连、周寿康等;西路啷当的教员先后有:陈腊荣、刘连生、钱书和、蒯三庚、束绥敖、郑树和、陈双庚等。“滩头”的授课曲目只传40 种,荤素各20,同时鼓励自编自创;“本头”的授课曲目有《红粉记》《卖花记》《白蛇记》等60 部。并规定每年农历四月十六和八月十六集中开两次行会。至此,“丹阳啷当艺人行会”正式运营,先后接纳会员近300 人。
二、“啷当”的发展与编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滩簧”等多剧种的普及,报名说唱丹阳啷当的艺徒剧减,盲艺人的演出范围开始缩小。据20 世纪50 年代初统计,常年演出的丹阳啷当不足40 人,传习的行会形同虚设。为保护和振兴丹阳啷当这门优秀的传统艺术,1958 年11 月,由丹阳县文教局开办、县文化馆代管的丹阳县文艺骨干训练班开班,训练班设置了演员和乐队两个专业,以一批现代小剧目和啷当基本曲调为教学内容,全县27 名年轻的文艺骨干参加了学习培训,训练班还组织学员编排了定谱定调定腔的《张木匠上北京》等四出小戏。
1959 年元旦,四出小戏在当地公演受到热烈好评,并被百姓称作“啷当戏”。丹阳县文化馆为全力抢救这一传统曲艺,遂在这次训练班的基础上,于当年1 月10 日成立了云阳剧团,同年9 月“啷当戏”被正式定名为“丹剧”,云阳剧团随之易名为丹阳县实验丹剧团。1960 年2 月实验丹剧团又被命名为丹阳县丹剧团。
1961 年11 月,由丹阳县丹剧团在啷当唱本基础上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砻糠记》赴宁公演,获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演出得到了全省戏曲界的高度评价和肯定,这也是“啷当戏”被定名为“丹剧”后丹阳县丹剧团演出的第一台传统剧目。此后一直到“文革”前夕,丹剧在剧目创作、移植、改编、整理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进展,首先在基本唱腔上解决了男女分腔的难题,并积累了男女唱腔60 多种、器乐曲牌40 多支;在表演上兼蓄了其他戏曲剧种之程式,逐步发展出了老生、小生、老旦、花旦、小丑等行当;在演出形式上吸取了京剧所长,在表演风格上兼收了越剧之优。
1966 年“文革”开始,丹剧团被认为是“复辟封资修”的“黑样板”而被解散。改革开放后的
1982 年丹阳县丹剧团恢复建制,1987 年12 月丹阳撤县设市,1992 年6 月由丹阳市丹剧团创排的大型现代丹剧《野塘婚礼》,代表江苏省参加文化部在福建泉州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获剧目奖和演员奖(展演点分“南北片”,分别于6 月和7 月在福建泉州和山东淄博举行),同时丹阳市丹剧团被文化部授予“天下第一团”光荣称号,获此殊荣的共有在两地展演的全国32 个稀有剧种的32 家院团。为更好地调配和发挥剧团力量,1994 年丹阳市丹剧团和丹阳市锡剧团合并为丹阳市戏剧总团,2021 年戏剧总团又经改制创建了丹阳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至2023 年11 月3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了“江苏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丹剧”列其中。而作为“丹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单位,丹阳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所承担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传承和传播职责,无论是在公司的发展路径、人才的培养引进、剧目的创作推介、演艺的深度提升、对外的文化交流、市场的渠道开拓、媒介的大众传播等方面都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开放式平台。在丹阳这块79 万人口、104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有为丹剧的振兴而奋力拼搏的丹阳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也有遍及丹阳城乡的近200 家业余性质的演艺团体,典型的有丹阳市云阳艺术团、丹阳市吴风楚韵艺术团、丹阳市金凤凰艺术团、丹阳市市民广场戏曲协会、丹阳市云阳街道大定船扬帆戏曲协会、丹阳市开发区双庙戏曲协会、丹阳市丹北镇戏曲协会、延陵镇新生艺术团、皇塘镇张埝艺术团等,他们共同构建成了丹剧保护与传承的网络式新格局,同时还培养出了自新中国以来的赵玉梅、华雪凤、卞兰萍、徐国定、唐宝琴、史怡、邹建生、金红霞、谢爱忠、步莉莉、倪开朗等丹剧艺术共五代传人。
丹剧是中华戏剧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其乡音乡曲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都使之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教化功能。丹剧艺术和我国其它戏剧一样,其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十年动乱”中丹剧团解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演出市场低迷,2004 年大型古装丹 剧《叔嫂冤》在“建设新农村,文化村村行”的送戏下乡中实现绝处逢生,2015 年再次陷入经营发展困境,2016 年演出自主收入超过百万元,直至2020 年底丹剧《槐荫记》在国家大剧院参加了我国戏曲界最高规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观看的央视新年戏曲晚会,乃至到了2022 年大型现代丹剧《凤先生》入选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投入剧目和江苏省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凤先生》还勇摘了江苏省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奖”。这些波澜起伏的历程似乎印证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趋势,一个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从“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 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个个有限的过程组成了无限的发展世界,事物的前进道路都将是迂回曲折的。
2023 年8 月,由上海戏剧学院、全国戏剧期刊联盟、田汉戏剧奖组委会、山东省艺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23 全国戏剧期刊联盟主编年会暨第37 届田汉戏剧评选活动”,在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举行,上述丹剧《凤先生》又荣膺了第37 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看到该剧本喜获一等奖,我不由想到了武汉大学教授邹元江在《文艺报》刊登的文章《濒危戏曲剧种的出路在哪里》,该文对丹剧《凤先生》的感慨尤为深刻,文中说,“用成熟优秀的剧作来带动剧种的保护与发展,不失为当下挽救濒危剧种的有效方式。被誉为‘汉剧之母’的山二簧、被称作古剧‘活化石’的梨园戏,包括丹剧等濒危剧种,都是因上演优秀的新剧目而走出剧种困境的成功范例,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近年来,丹剧影响日隆,在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同时,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应当是“作为濒危戏曲剧种灵魂的音乐声腔”(见《濒危戏曲剧种的出路在哪里》)。邹元江在文中所讲的“濒危戏曲剧种”指的就是富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音乐声腔,它是丹剧的真正灵魂,也是丹剧的内核所在!这正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因为丹剧的源头乃“啷当说唱”也。
(作者为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研究馆员)
- 上一篇:镇江“乡学”——甲骨文研究
- 下一篇:镇江报业史及相关文化研究路径浅探